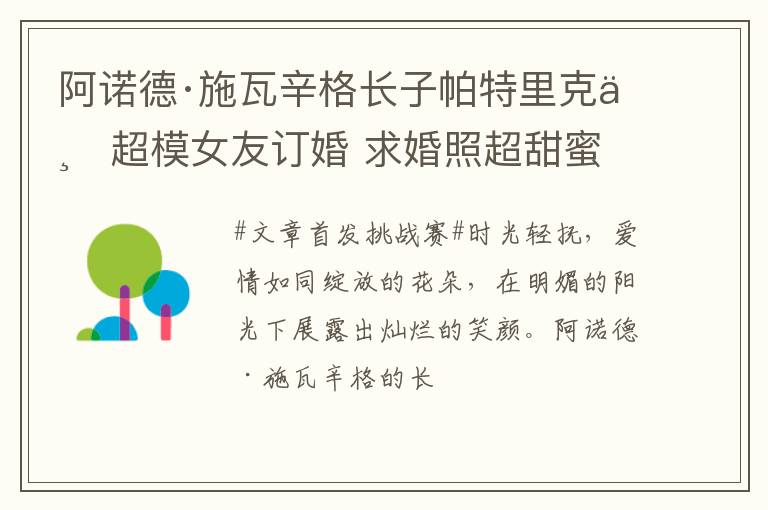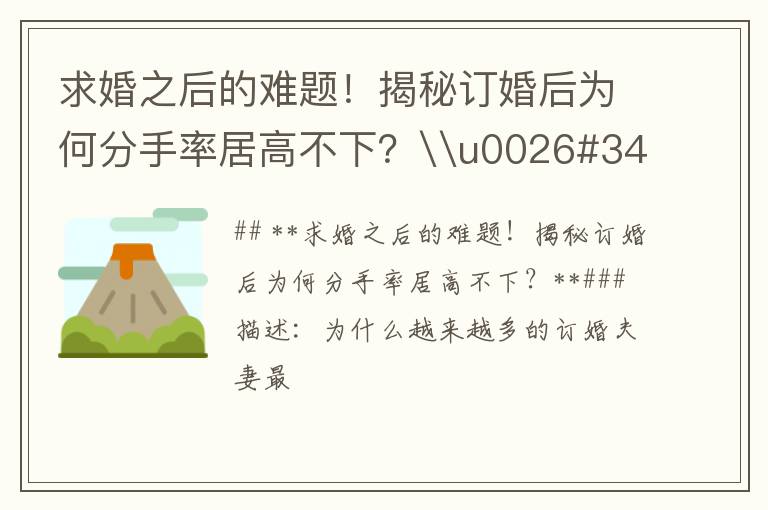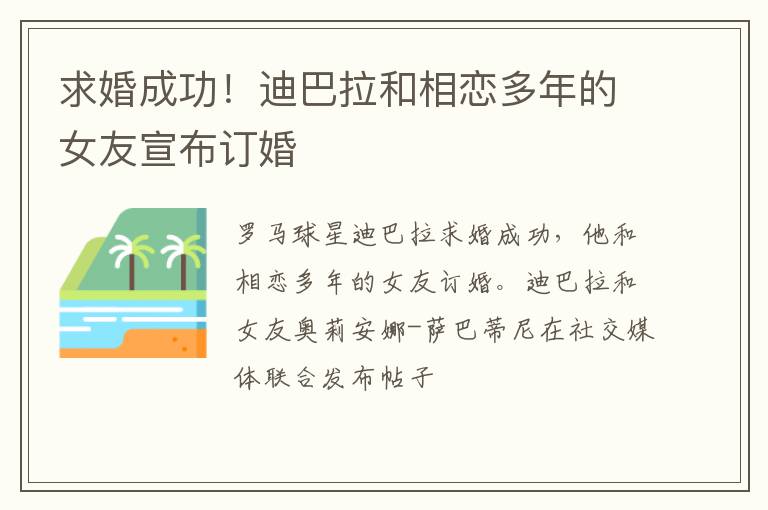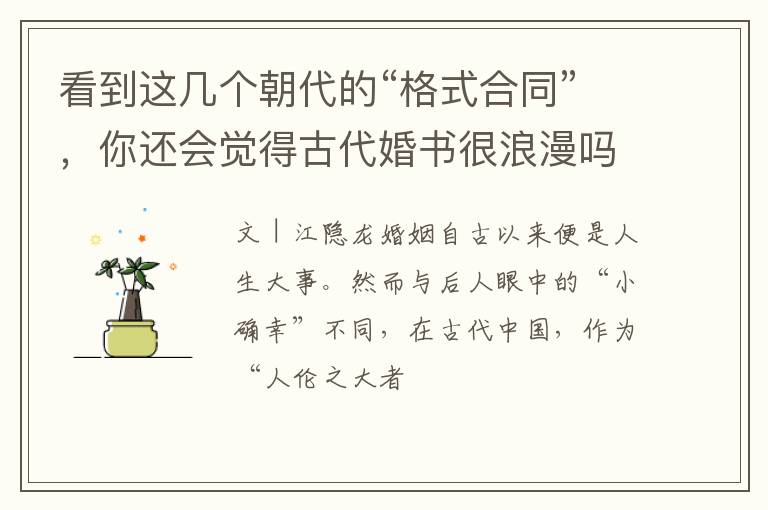
文 | 江隐龙
婚姻自古以来便是人生大事。然而与后人眼中的“小确幸”不同,在古代中国,作为“人伦之大者”的婚姻一直承载着宗法社会下“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的政治使命,因而为历朝历代所重视,并呈现出严肃的一面。对于婚姻的解读与规定,有宣扬纲常名教之义者,如《魏书·帝纪》中所言:“夫婚姻者,人道之始。是以夫妇之义,三纲之首;礼之重者,莫过于斯。”也有弘扬时代精神者,如195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开宗明义:“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
岁月荏苒,后人很容易通过想着史籍的描述去勾勒婚姻制度的架构与诉求,但却很难通过这些描述去还原、回味婚姻一事在古人心中的细微感知。所幸,在这些宏观的礼仪构建之下,尚有一些更为微观的物件流传下来,用相对细碎的笔触将一代代男婚女嫁记述得丝丝入扣,为后世留下一幅更为清晰详尽的“婚姻礼法图”——这一物件,就是婚书。
顾名思义,婚书自然与婚姻相关,但其边界却颇难界定。古代中国并无严格意义上的“结婚证”,婚姻缔结过程中所涉及的婚书种类繁多、功能各不相同,且随不同朝代的律法频繁变化,故只宜泛泛而论,将婚姻缔结过程中所用的文书统称为婚书。当然从广义上来讲,婚姻解除所用的休书、放妻书等也应当归为婚书,但在“合二姓之好”之义的视角下,这一类婚书在宗法社会的也只合被归为例外情况了。不过,仅将婚书的范围局限于“婚姻缔结过程中所用的文书”,并不会让这一文字载体变得更富人情味,因为婚书所代表往往不是古人流露的柔情蜜意,而是壁垒森严的等级制度。

新中国第一部法律:婚姻法
六礼:宗法制中的婚书之源
中国的传统婚姻礼仪有“三书六礼”之说。三书为六礼过程中所用各类婚书的概括,其内容指向六礼最为关注的核心要素;而六礼大体而言是指古代中国婚姻缔结所需要历经程序。之所以要加上“大体而言”四字,是因为六礼程序本身在不同朝代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或繁复或简略难以一概而论;同时六礼之仪也并非面向社会所有阶层,《仪礼》中论及六礼的内容载于“士昏礼”一章,可见其礼只通行于士大夫阶层。只是这一制度历千年而不废,故而能够在千年的岁月流转中成为中国的传统婚姻习俗的代名词。
六礼最早且相对完备的记述见于《礼记》《仪礼》。《礼记·昏义》中明确了婚礼的“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等程序,而《仪礼·士昏礼》则进一步对六礼的细节进行了描述,如“纳采用雁”“宾执雁,请问名,主人许”“请期用雁”等。详细而论,六礼程序主要如下:
一为纳采,又称“提亲”“执柯”“说媒”。男方父母请媒人备好礼物向女方父母求婚,以区别男女之间的“私约”;二为问名,又称“求庚”“求八字”。女方父母在纳采之后若有意结姻,男方父母则请媒人进一步询问待嫁女子的姓名、生辰等信息。双方父母在此阶段过门户帖,上书姓名、年龄、上三代名号、官职等,以确定辈分、防止近亲结婚。三为纳吉,又称“合婚”“批八字”。双方父母在此阶段过八字帖,若得到吉兆,男方父母便“复使使者往告”。四为纳征,又称“纳币”“秆聘”“茶仪”,男方在纳吉之后正式送聘礼至女方父母家定婚,女方父母则以接受聘礼表示许婚。五为请期,又称“择日”。男方父母确定婚期并将婚期帖送到女方父母,女方父母同意后回帖,称“完聘”。最后的亲迎,男方亲自代表父母、宗族,将女方迎娶至家。

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为六礼的正式名称,如提亲、求庚、择日等称谓则是六礼在后世流变形成的或雅或俗的别称。值得一提的是,《礼记》中只点明了前五礼而未直接确定亲迎之说;而《仪记》中则记载了“若不亲迎,则妇入三月,然后婿见”之后的礼仪要求,可见周朝礼制中亦以亲迎为要,若因故未能完成,尚需要通过事后的程序进行弥补。
六礼之制殊为繁复,而周朝也的确有充分的理由对婚姻进行严格约束。从政治层面来看,一夫一妻多妾制、嫡长子继承制的稳定需要一套完善的婚姻制度进行维护,而宗族的稳定发展也需要通过“同姓不婚”达到避免“其生不蕃”和“娶于异姓,所以附远厚别”的目的。从六礼所规定的种种条件来看,周朝的婚姻更近于两个家族之间的联姻而非两个人的选择,婚姻当事人自始至终没有决定权,新郎甚至直到六礼的最后一个环节亲迎才有可能接触到新娘,从中自能品味出周人对“婚姻”二字的理解。
周朝时虽然没有发展出完善的三书,但不难看出六礼的每一环节均有有“交相授书”的文字佐证,这些文字佐证便是后世求婚书、龙凤帖、迎亲书等婚书的雏形。不同朝代的婚书虽然形式不尽相同,但其代表的程序及内容基本一致,从中也足以感受到周礼的重大影响。

正如《仪礼》中的章目名“士昏礼”一样,有周一朝“礼不下庶人”,六礼也仅流行于士大夫之家。那对于庶人而言,婚姻一事是不是便无礼可言了呢?
周朝庶人虽不通行六礼,但并不意味着婚姻缔结可以“妄为”。《孟子·滕文公》中载:“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在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情况下“私定终身”,甚至会落入“父母国人皆贱之”的境遇,可见庶人之间结婚依然有相应程序。
相对于语气严肃的《孟子》,富有浪漫主义的先秦诗歌同样若隐若现地提到了周朝民间婚姻。《诗·齐风·南山》的“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可”、《诗·幽风·伐柯》的“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何?匪媒不得”,均明确地指出了媒人在庶人阶层所扮演的角色;而《诗·卫风·氓》的“尔卜尔筮,体无咎言……非我愆期,子无良媒”等句,更点明了即使是庶人,也会在婚前进行占卜。若严格依照六礼,不太可能出现已经“尔卜尔筮”却依然“子无良媒”的情形,从中可以推出周朝庶人阶层缔结婚姻的程序应当是六礼的“简化版”。

如果说周朝庶人的婚礼仅仅是六礼的简化,那周朝庶人的婚书则另有一幅截然不同的面孔。《周礼·地官·媒氏》载:“媒氏掌万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书之。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
周朝已经设定了专门的官员媒氏“掌万民之判”,并监管男性三十而娶,女性二十当嫁。在婚嫁过程中,对于“判妻入子”的情形,还需要专门记录。所谓“判妻入子”,杨天宇在《周礼译注》中释为“再嫁或带着儿子再嫁”,江永又补充“防其争讼也”,这说明媒氏所书的内容并不针对为“万民”的男女占卜确定吉凶,而仅仅出于律法角度意图厘清双方权利义务,以避免诉讼。为了保证青年男女在适婚年龄婚嫁,朝廷甚至扮演了“公媒”的角色,在中春之月“令会男女”——相对于士大夫阶层繁复而保守的六礼,这些规定显然更为“奔放”。
从政治层面来看,同样能看出这一“公媒”制度的目的。庶人婚配,对繁殖人口、扩充兵源、稳定税收方面有重要意义,故而由专员管理,并尽可能地创造适婚男女相识的机会。庶人之间的婚礼依然需要通过媒人进行,一方面可能是为了巩固宗法制而避免私约的出现,另一方面也很可能是朝廷借媒人实现对庶人阶层婚姻的控制。
整体而言,周朝的婚书呈现出两副面孔:士大夫阶层的婚书更偏重于礼,以保护宗族利益为重;庶人阶层的婚书更偏重于法,以调整百姓权利义务为重。中国古代婚书在形成伊始就天然具有极强的实用主义色彩及等级制度,感情之事反而自始缺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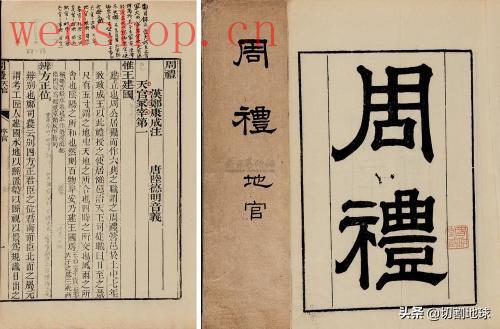
秦至唐:礼制与法治的合流
秦朝统一后以法家治国,用中央集权制、郡县制代替了周朝的宗法制,婚姻中的礼教色彩也被一并去除。结婚缔结的资格变得统一而刚性,据《睡虎地秦墓竹简》中载:“男子身高六尺五寸,举弱冠之礼,即可成婚;女子身高六尺二寸,行许嫁,即可成婚。”同时婚姻生效的程序也非六礼或“媒妁之言”,民间婚书更无法律效力,唯一能证明婚姻是否生效是是否到官府进行了登记。《法律答问》中载:“有女子甲为人妻,去亡,得及自出,小未盈六尺,当论不当?已官当论,未官不当论。”此处的“官”做动词,指至官府登记,从中可知秦朝婚姻是否成立以登记为准——与此相对,婚姻的解除也以登记为准,“弃妻不书”的行为同样违反秦朝律法。
秦朝二世而亡,不过其“法依治国”的策略却部分为后世所吸收。汉朝成立后,很快在士大夫阶层恢复了早已崩坏的周朝礼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两姓之谊、三书六礼重新出现,如《白虎通义》所言“男不自专娶,女不自专嫁,必由父母。须媒妁何?远耻防淫佚也”一句,便是对“父母之命”的学理解释。而针对庶人阶层,汉朝又效法秦制以法家管控,通过均田制、租调制等开始了严格的户口登记制度,将庶人婚姻缔结牢牢纳入法律的控制。
如果秦朝“万世而为君”,那婚书很可能从此被定型为官府所发放的婚姻凭证,中国传统婚书的发展史将会是另一番景象。汉朝之后,六礼的复兴导致三书重新被士大夫阶层所重视,最终在魏晋时期孕育出了六礼版文。

杜佑所撰《通典》中载:“东晋王堪六礼辞……礼版奉案承之。”晋朝六礼中已经开始使用这种六礼版文,版左书“纳采”二字,版中写男方父亲、媒人的名字,并书礼文。《全晋文》中有王羲之所作的《与郗家论婚书》,完整地体现了当时六礼版文的格式内容:
“十一月四日,右将军会稽内史琅玡王羲之,敢致书司空高平郗公足下。上祖舒散骑常侍抚军将军会稽内史镇军仪同三司,夫人右将军刘缺女诞晏之、允之,允之,建威将军钱塘令会稽都尉义兴太守南中郎将江州刺史卫将军,夫人,散骑常侍荀文女,诞希之仲之,及尊叔廙平。南将军荆州刺史侍中骠骑将军武陵康侯,夫人雍州刺史济阴郗说女,诞顺之胡之耆之美之,内兄胡之,侍中丹阳尹西中郎将司州刺史,妻常侍谯国夏侯女,诞茂之承之羲之,妻,太宰高平郗鉴女,诞玄之凝之肃之徽之操之献之。肃之,授中书郎骠骑谘议太子左率,不就,徽之黄门郎,献之字子敬,少有清誉,善隶书,咄咄逼人。与公宿旧通家,光阴相接,承公贤女,淑质直亮,确懿纯美,敢欲使子敬为门闾之宾。故具书祖宗职讳,可否之言,进退惟命羲之再拜。”
《与郗家论婚书》是现存最早的婚书文字记载,为王羲之为其子王献之求亲所做。这封婚书洋洋数百字,其内容大半在讲述王氏一门的五代职官履历,以证明其身世足以与郗氏门当户对,直到最后才谈及主角王献之“少有清誉,善隶书,咄咄逼人”和郗道茂“淑质直亮,确懿纯美”。通体而言,《与郗家论婚书》中豪门士族之间联姻意味非常明显,这封婚书与其说是王献之与郗道茂的婚书,倒不如说是琅琊王氏与高平郗氏的婚书。

王羲之所处的时代正是门阀士族的时代,士大族阶层极重门第出身,故而六礼中的等级制度被层层加码。反观庶人阶层,纵然想要依六礼书写婚书,又怎如何有这般多的历史供其书写呢?这便是魏晋南北朝时代的“礼不下庶人”——个中之义,孔颖达《五经正义》中如此解读:“礼不下庶人者,谓庶人贫,无物为礼,又分地是务,不服燕饮,故此礼不下与庶人行也。”依孔颖达的解释,“礼不下庶人”尚是考虑到庶人贫困,无力操办筵席置办礼物,故不以礼仪为难庶人。不过究其根本,庶人阶层地位低下,其权利只能从属于士大夫阶层,极端如北齐武平七年(563年)所下的诏令,甚至直接要求“括杂户女,年二十以下,十四以上未嫁者,悉集省,隐匿者家长处死刑”。杂户是南北朝时期地位高于奴隶的一个阶层,在这道诏令中,杂户女与物品无异,若其自身权利都无法保障,还要依六礼操办婚姻大事,便显得荒唐了。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婚姻礼仪以周朝六礼为主且更重门第,这一倾向影响深远,直到唐朝的士大夫阶层依然保持着“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的惯性。不过在唐朝,“三书六礼”之制又有了更进一步的分化。
有唐一朝,六礼依然是士大夫阶层婚姻缔结所必需遵守的制度。《唐律疏议》载:“妻者,传家事,承祭祀,既具六礼,取则二仪。”《大唐开元礼·嘉礼》更明确了六礼的使用范围包括纳后、皇太子纳妃、亲王纳妃、公主降嫁、三品以上婚、四品五品婚、六品以下婚——作为门第的体现,六礼的通行范围上至皇族下至各级品官,与庶阶层无涉,这可以说是唐朝礼制的一面。

然而唐朝同样有法治的一面:正是在唐朝,婚书正式进入法律文本。《唐律疏议·户婚》规定:“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谓先知夫身老幼疾残养庶之类)而辄悔者,杖六十;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财(聘财无多少之限,酒食非。以财为酒食者,亦同聘财)亦是。若更许他人者,杖一百;已成者,徒一年半。”可以看出,唐朝承认民间婚书甚至是私约的法律效力,这一点与秦朝“已官当论,未官不当论”截然不同;同时唐律中所规范的主要是婚书所带来的财产纠纷问题,更直接明确了聘财在婚约中的地位,这使得唐朝的婚书在具有礼制色彩的同时,同时具备了契约性质——这可以说是唐朝法治的一面。
整合而论,六礼在唐朝为士大夫阶层通行的婚姻礼仪,而婚书则面向所有唐人,具有更强的普世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婚书虽非唐朝首创,但却在唐朝焕发了新的生命。唐朝婚书为复书式,由正书和别纸组成。正书多虚文套话,表达求婚之意;别书记载男女双方姓名、年龄等基本信息。男方父母未婚所用的叫通婚书,女方父母收到后若同意将回书,这封书则是答婚书。虽然庶人阶层婚姻缔结不要求齐具六礼,但作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婚书,依然有较强的形式感,吴玉贵著《中国风俗通史·隋唐五代卷》中描写到婚书当“用好纸,楷书写成,放入杨木或楠木的礼函中。礼函的尺寸有重要的象征意义,长一尺二寸,法十二月;宽一寸二分,象十二时;木板厚二分,象二仪;盖厚三分,象三才;函内宽八分,象八节。”
唐朝婚书代表了礼制与法治的结合,是唐朝婚姻制度的一大创新。不过这一创新在当时也遭受到了非议,如颜真卿便曾于建中元年(780年)上奉,认为婚书“出自近代,事无经据,请罢勿用”。颜真卿抵制婚书的理由是其“事无经据”,然而这一“事无经据”的婚书不但没有被取缔,反而生命力愈加顽强,成为中国婚姻制度史上殊为重要的物件。

宋至清:当婚书成为格式合同
随着时代的发展,唐朝之后中国社会构成出现了极大的变动,婚姻缔结过程中双方对出身门第的关注度相较前朝有所下降,形成“自五季(五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的局面。婚姻制度中士大夫阶层与庶人的分野变得相对模糊,这一背景也间接决定了宋朝婚姻礼制的改革方向。
“崇文抑武”的宋朝极重视礼制。彭利芸在《宋代婚俗研究》中评价“惟宋代礼法,上承仪礼、周礼,礼记为本;后集汉、晋、唐的大成”,应当说非常中肯。然而,也正是宋朝对六礼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一方面,宋朝从法律角度扩大了六礼的适用范围,使其从皇族、品官推广至整个庶人阶层;另一方面,宋朝“并问名于纳采,并请期于纳成”,将六礼简化为四礼,同时对六礼中所用器物进行了变通规定,如庶人若无法取得六礼所需的雁,“听以雉及鸡代”。这两个政策可谓相辅相乘:要扩大适用范围就必须简化流程,因为于庶人阶层很难支撑六礼的成本;而简化流程也自然对扩大适用范围起到推动作用——可以这样说:六礼正是在宋朝的改制之下,正式成为中国各阶层共同的习俗。事实上,改制之后的六礼不仅因其简洁而逐渐通行于两宋民间,更成为后世元、明、清三朝婚礼制度的基础;若无此改制,六礼古制能否被承袭、能承袭多少,便真的要打上一个问号了。
宋朝在六礼的框架上改革甚多,但其婚书依然保持着唐朝的基本风貌,且更为细致。依《东京梦华录·娶妇》载:“凡娶媳妇,先起草帖子,两家允许,然后起细帖子,序三代名讳,仪亲人有服亲田产官职之类。”此处的帖子是经媒人说和之后写成的局面契约,男方、女方各执一份,第一次用相对简略的草帖子,之后再用信息丰富的细帖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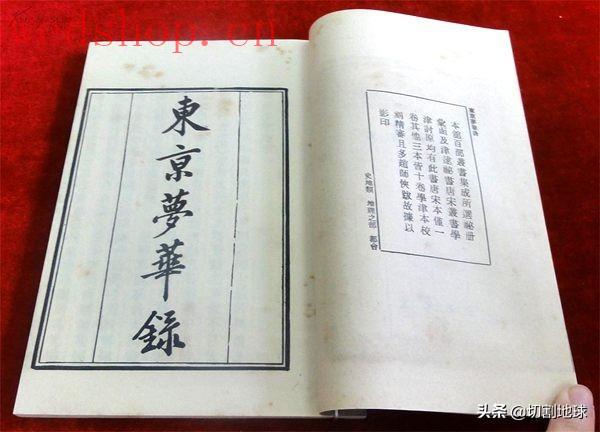
《梦梁录·嫁娶》中的记载与此相似:“嫁娶之礼,先凭媒氏,以草帖子通于男家。男家以草帖问卜,或祷忏,德吉无尅,方回草帖。”问卜祷忏之举,即融入了六礼中的纳吉。此时回的草帖,同样需书写男方的基本信息以供女方问卜,若同为吉卦则“媒氏通音”,开始书写定帖。相对于草帖,定帖需定明“叙男家三代官品职位名讳,议亲第几位男,及官职年甲月日吉时生,父母或在堂,或不在堂,或书主婚何位尊长,或入赘,明开,将带金银、田土、财产、宅舍、房廊、山园,俱列帖子内”,而女方此时的回帖同样要列明“议亲第几位娘子,年甲月日吉时生,具列房奁、首饰、金银、珠翠、宝器、动用帐幔等物,及随嫁田土、财产、宅舍、房廊、山园等”。
将宋朝的定帖与《与郗家论婚书》相比,会发现两者在叙述男家官品职位名讳方面有相同之处,唯后者又多了一丝世俗气息,需要将“金银、田土、财产、宅舍、房廊、山园”等财产信息挑明。时过境迁,魏晋时代单纯以出身门第论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宋朝经济发达,民风竞奢,其婚书自然而然沾染上了世俗之气。
对于这一趋势,宋人也有不同呼声,《东京梦华录》中亦感叹“今世俗之贪鄙者,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至于立契约云,某物若干”,不过这种“贪鄙之风”反过来也使宋朝的婚书更具法律意义。《刑统赋解》中载:“婚姻书文,开写如镜……婚书已立,各无隐讳……若有妄冒,官断听离。女家辄悔,科罪六十,男家自悔,聘财不追。”婚书——尤其是定帖中所书的财产信息均将视为男女双方的承诺,需对其负法律责任,这其中所包含的契约精神,又远非前朝所能相比。

宋朝这一重婚书契约属性极为实用,因而为后世所继承。元朝《元典章·户部四·婚礼》中更为直接地规定:“今后但为婚姻议定,写立婚书文约,明白该写元议聘财钱物……凡婚书,不得用彝北语虚文,须要明写聘财礼物。婚主并媒人各各画字。女家回书亦写受到聘礼数目,嫁主并媒人亦合画字。仍将两下婚书背面大书‘合同’字样,分付各家手执。如有词语朦胧,别无各各画字并‘合同’字样,争告到官,即同假伪。”
为了满足婚书的法律要求,元朝刊印的应用文范本《新编事文类要启札青钱》中也辑录了“婚姻四六启式”的各类格式婚书,包括“请媒启”“谢媒启”“求亲启”“开封启”“问名启”“聘启”“请纳采日期启”等。与唐制相同,这些婚书均为复书式,且据双方身份、地位、职业不同分别开列,语气用词亦各有差别。至此,婚书虽依然是六礼的组成部分与文书载体,但其法律意义已经愈加明显,甚至远远超过了其礼制色彩。
宋元以降,六礼、婚书的世俗意义及法律色彩一再加强,这一趋势依然为明清两朝所承袭。《明会典》规定:“凡男女订婚之初,如有残疾、老幼、庶出过房乞养者,务要两家明白通知,各从所愿,写立婚书,依礼聘嫁。”婚书的主要用途除证明婚姻合法性之外,主要在于厘清男女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当然,明朝对婚书的严格要求,除了法律本身所需的精确之外,也因媒人为促成婚事取得“谢媒礼”而故意“俊的矜夸,丑的瞒昧”,以至于男女双方常常无法得到对方的真实信息,而这一情形本身,也正是婚书“世俗化”的必然结果。

时至清朝,婚书进一步简化,以至于虚词、套话尽数被省略,直接以男女双方基本情况为主,这一情形在清末尤其明显,如宣统年间的婚书甚至不写祖上信息,男女双方的定与回不过寥寥数十字:
请书式为:“仰候玉音:眷姻弟某某某率男某某顿拜,冰人某某,亁命某年某月,宣统年月日。”允书式为:“谨蒙金诺,眷姻弟某某某率某女顿拜,坤命某年某月,宣统年月日。”
虽以明确权利义务为要,但如此简略的婚书也着实令人唏嘘。如果说从周朝繁复冗长的六礼到宋朝大刀阔斧的改革是婚姻制度的进化,那从洋洋洒洒的《与郗家论婚书》到宣统年间毫无情感文采可言的格式婚书,便不知要做何解释了。

结语
中国古代婚书的发展源远流长且脉络复杂,但依然可以提炼出一个规律:婚书自古便分为两端,其一是士大夫阶层在六礼过程中所需的文书,其二是朝廷为管理庶人阶层婚姻而发放的文书。前者是礼制的体现,后者是法治的代表,而二者的分野又标志着两套不同的管理方式。
唐宋时期,六礼在向庶人阶层扩散的过程中逐渐简化,婚书中的礼制功能与法治功能也渐渐合流,既能与简化后的六礼相结合,同时又具备了明确权利义务及契约关系的功能。宋后,婚书的法律色彩逐渐加强,最终在清朝末年剪去了所有枝蔓浓缩成一纸凭证。民国时期,婚书格式愈加固定化,男女双方只要到书局或纸店习一式两份的“订婚书”,填上相关信息,由结婚人、介绍人、主婚人、证婚人在婚书上签章,婚姻关系就正式成立了——唯独不同的是,根据1914年北洋政府《关于人事凭证贴用印花条例》和1934年《印花税法》婚书须贴印花、依法向国家纳税方才受国家保护。
自周朝“媒氏掌万民之判”以降,婚书的演变无不与当时特殊的经济发展、政治制度、文化思潮紧密相关。而纵观历朝婚制的发展,“三书六礼”究竟能不能在总体上代表中国古代婚姻礼仪,又成了一个问号。真正的六礼只通行于士大夫阶层,而当它飞入寻常百姓家时,便不再是真正的六礼了。
个中滋味,当后人翻阅历朝林林总总的婚书自有不同感悟,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婚书虽与婚姻相联,却终究与感情无关。

郑重声明: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文章仅为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如作者信息标记有误,请第一时间联系我们修改或删除,多谢。